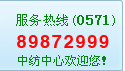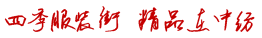“在中国,服装也是政治”在汉语世界里,“衣冠”本来就具有特殊的意味。它代言着文明、开化与正统。但衣冠只是路径,只是表达,它通往的都是自己千年不变的道路。
1955年,在《六亿蚂蚁》一书里,法国记者罗伯特·吉兰这么描述着他的中国印象:“不管走到哪里,人们都穿着蓝布衣服。……姑娘们也穿着长裤,除了下垂的头发或农民式的辫子,她们穿得跟男人一模一样。……一群群人,一个个都像是刚从蓝墨水中洗澡出来,一身去不掉的蓝色。”
吉兰由此感慨,这个国家是一座“蚂蚁山”,六亿民众是栖息其中的“蓝蚂蚁”。此后二十余年,随着《六亿蚂蚁》的持续畅销,这个说法频繁出现于西方报刊。“蓝蚂蚁”成为大陆中国人的代名词了。
撇除傲慢与偏见,吉兰的说法并不夸张。1978年冬天,当皮尔·卡丹夹杂在大群游客间,缓缓走向八达岭长城时,他看到的依旧是一个蓝咔叽布的海洋。然而,与吉兰不同,这个威尼斯破产商人之子,这个出身贫寒、当过裁缝学徒的巴黎时装设计师,此时却在这个冻原般的国度,嗅到了别样的气息。
这个冬天,皮尔·卡丹产生了在北京举办几场时装演出的想法。他后来谈到,“这是个疯狂的念头。……我曾以为这是不可能的,但我还是做到了。”
的确举办时装演出此时不啻于天方夜谭。这一年冬天,尽管坚冰初破,这个广袤而神秘的国度依旧色调森严、禁锢处处。对西方的舶来品,这个蓝黑灰的世界不仅疑虑重重,甚至心怀敌意。
“大约11月下旬,对外友协转来了报告,说一个法国人要举办时装演出。对这类活动,当时我们闻所未闻。……”二十多年以后,在北京中纺里的一处公寓,一个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耄耋老者追忆着当年的情景:“当时,改革开放的舆论已经抬头,但是大氛围还是冷色调的。这个事情,不敢拍板,没有人敢拍这个板。……”
在皮尔·卡丹的反复游说、活动下,当年年底,由纺织工业部牵头,外贸部、轻工业部派员参与,一小群官员进行了“三部会商”。然而,几次会商后,这个报告还是被搁置了。
山重水复疑无路。直到次年初春,这些官员看到了那顶帽子。
这一年农历春节,也就是1979年1月28日,邓小平开始了为期八天的美国访问。五天以后,在德克萨斯州的一个竞技场,这个刚刚被《时代》周刊评为“年度风云人物”、并以48个整版篇幅详尽报道的“新中国的梦想家”,大大方方地戴上了两名女骑士送来的白色牛仔帽。这个象征性的细节,不仅引发了世界范围的热烈报道,它也让这场行将夭折的演出柳暗花明。
牛仔帽是一个符号,是一种政治隐喻。对此,这些官员心领神会,他们一改拖沓和观望,迅速准许了这次演出。与此同时,一些限制性要求也出现了:演出不报道、不宣传,“尽量低调”;不对公众开放,仅限外贸界、服装界官员及专业人士进行“内部观摩”;各单位在发放门票时,应严格把关,挑选“思想素质过硬”的观众……此外,原定在北京举办的三场演出,也被一分为二:北京首演之后,另外两场演出将在上海进行。
正是这个决定,催生了中国第一支时装模特队。
1988年2月,服装设计师皮尔·卡丹先生(左二)接受记者采访。
初次登台
在北京的首演,很难用“成功”或“失败”来评价。1979年3月10日,当8名法国模特和4名日本模特缓缓走上民族文化宫的一处新搭就的T型台时,现场的气氛无比凝重、紧张。作为亲历者之一,新华社记者李安定后来谈到,当时场内“人满为患”,几百名观众大多“穿着蓝灰制服、屏住呼吸”;另一位在场观众的回忆更为细微:“那些女模特出现时,我产生了一种晕眩的感觉。……坐在我附近的观众,也一个个脸色严峻,表情变化得很厉害……”
与北京相比,上海的氛围宽松了许多。以入场券发放为例,主办方仅有三点要求,“专业对口”、记录姓名,以及入场券不得转让。这么一来,不仅专业官员,许多服装设计师也得以入场观摩。二十多年以后,上海服装公司设计师徐文渊回忆说,“当时我一看,他表演的这些服装,款式新颖独特,色彩也绚丽多彩……”
服装之外,那些艳妆的模特,更唤醒了许多老上海的记忆。毕竟,距离十里洋场的上海滩时代,此时还不过三十年。徐文渊记得,演出结束后,他和自己的顶头上司、上海服装公司经理张成林一起回家。路上,张成林忽然冒出了一句话:“你看,这个立体宣传多好啊,我们也来搞一支,怎么样?”
徐文渊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“他会讲这样的话?行吗?我们国家行吗?那么保守、那么封闭的那个年代……”徐文渊后来说:“我看着他,我讲,你敢的话,我大力支持你。”
出乎徐文渊意料的是,张成林固然不是一时兴起,主管部门也并非铁板一块。几天后,由徐文渊草拟、张成林定稿的组建模特队方案书,到达了上海市手工业局局长刘伟胜的案头。据说,刘伟胜当天就召见了他们。
“看了这个方案,(刘伟胜)基本上赞同。……”徐文渊说:“但是,对时装模特几个字,他犹豫了半天。他讲,模特儿,这是外国的称呼,好像有点低级趣味的感觉。他讲,这样吧,在我们国家不要叫模特,就叫时装表演演员,怎么样?……”
此外,业余性质、男女混杂、强调“纺织工人”的身份……也成为组建表演队的几个条件。顺理成章地,徐文渊出任了表演队领队。
变化
作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,张成林、刘伟胜等人表现出了足够的勇气。然而,作为历史中的小人物,他们依托的背景,实则是一个坚冰初破、含苞待放的初春图景。
早在1978年夏天,许多西方观察家就注意到了暗流的涌动。这一年6月8日,《基督教科学箴言报》的记者这样描述北京街头的变迁:“虽然单调的灰色和蓝色衣服仍然是标准的服装,但是妇女开始涌向百货商店,从有限的供应品种中选购衣料。在城市,卷发和电烫发型开始时兴。北京排队最长的地方是理发店。”与此同时,传自香港的喇叭裤在广州街头悄悄出现,这种裤子改变了女装裤右侧开口的习惯。作为流行文化的最初冒险,它被许多人认为“不男不女”,并一语双关地说它“颠倒乾坤”,然而,短短几年时间,它迅速地风行于各处城乡……
不仅民间,官员们的态度也悄悄变化着。如果说,允许皮尔·卡丹举办演出,不过是少数官员的大胆举动的话,那么,就在皮尔·卡丹首演次日,路透社的一条消息折射了更多官员的内心:“尽管那些观众都是经过严格审查的,但走出民族文化宫时,男人们大多解开了风纪扣。一些胆大的姑娘更把裙子提了提,露出雪白的膝盖……”
也就是说,演出事实上大获成功。它唤醒了几百名中国官员对美、对差异化世界的本能向往。正是这种汹涌的、席卷了大多数人的暗流,让张成林、刘伟胜们萌生了组建表演队的想法,从而开风气之先。
尽管如此,表演队的组建,也远谈不上一帆风顺。
模特队
上海服装公司下属有八十多个工厂,青年男女数以万计,萌生想法之初,张成林就决定“到工厂去挑选(模特)”。但按国际惯例,入选条件应包括身高、胸围、背宽、乳 房间距等硬指标。徐文渊为此万分为难:“我这一看,复杂得很啊!……这些都是隐私,在当时可以说是最大的隐私,你怎么打听?怎么选?”
无可奈何之下,徐文渊只好大打折扣:男演员身高179厘米以上;女演员身高165厘米之外,三围应分别在80厘米、60厘米和80厘米以上。最后,“下半身应比上半身长八公分”……
更困难的还在后头呢。1979年春夏,中国女工的普遍形象,是蓝咔叽布工装、肥大长裤,以及一双深颜色的塑料凉鞋。即使得风气先的上海,那些最时髦的青年男女,相互攀比的也不过是的确良衬衫、回力牌球鞋。难道这些入选男女真有勇气在T字台上招摇过市?难道她们的父母会忘记上海的文革,正是从红卫兵上街剪“小脚裤”开始的么?
“当时张经理要求我们,要做到‘四个通’。”徐文渊后来回忆,“思想要通,家庭要通,本人要通,朋友要通。要‘四通’……”
“四通”中,最困难的是家庭这一关。徐文渊记得,一名条件很好的杨姓男青年,因为父母坚决反对、“怕孩子学坏”,而不得不放弃了。即使是最终入选的那些成员,也无一例外地面对着巨大的家庭阻力:年仅19岁、刚刚参加工作两个月的柴瑾,长期不敢向母亲吐露真相;思想开放、敢想敢做、被称为“性格演员”的徐萍,干脆向所有家庭成员封锁了消息……
整整八个月以后,时装表演队终于组建完毕了。这一年秋天,在一处清理出来的库房里,表演队首批成员开始了自己的训练。他们中,包括了七个小伙子以及十二位姑娘。